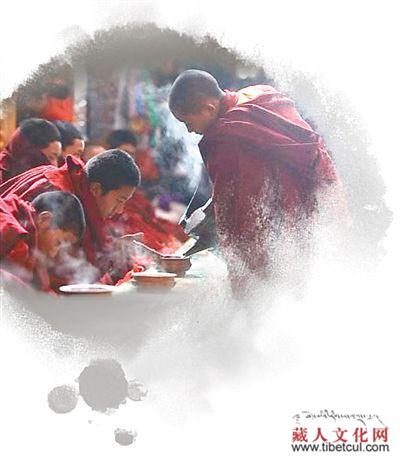
еҲ¶еӣҫпјҡи”ЎеҚҺдјҹ
еҚғзҷҫе№ҙжқҘпјҢз”ҹжҙ»еңЁйӣӘеҹҹй«ҳеҺҹзҡ„и—Ҹж°‘ж—ҸдёҺиҢ¶з»“дёӢдәҶдёҚи§Јд№ӢзјҳпјҢе Әз§°е—ңиҢ¶еҰӮе‘ҪпјҢ他们еҗҢж ·жҠҠиҢ¶иһҚе…ҘдәҶз”ҹе‘ҪпјҢиһҚе…ҘдәҶж–ҮеҢ–пјҢиҝҳз§ҜзҙҜдәҶдё°еҜҢзҡ„йҘ®иҢ¶з»ҸйӘҢпјҢеҲӣйҖ дәҶзӢ¬е…·зү№иүІзҡ„иҢ¶ж–ҮеҢ–гҖӮ
пјҲдёҖпјү
и—Ҹж—Ҹж°‘й—ҙжңүдёӘи°ҡиҜӯпјҡ“е®ҒеҸҜдёүж—Ҙж— иӮүпјҢдёҚеҸҜдёҖж—Ҙж— иҢ¶”пјҢиҜҙзҡ„жҳҜпјҢиҢ¶дёҚд»…жҳҜж—Ҙеёёз”ҹжҙ»зҡ„еҝ…йңҖе“ҒпјҢжӣҙжҳҜй«ҳеҺҹз”ҹеӯҳзҡ„еҝ…еӨҮжқЎд»¶гҖӮеҸӨж—¶иҘҝи—ҸдёҚдә§иҢ¶пјҢиҢ¶еҸ¶дҪ•ж—¶иҝӣе…ҘиҘҝи—ҸпјҢе°ҡж— зЎ®иҜҒгҖӮеҸӨд»ЈжұүиҜӯжҠҠиҢ¶еҸ«“ж§ҡ”пјҢи—ҸиҜӯж—¶иҮід»Ҡж—ҘиҝҳжҠҠиҢ¶еҸ«“ж§ҡ”гҖӮ
и—Ҹж—Ҹж°‘й—ҙжөҒдј зқҖиҝҷж ·дёҖдёӘж•…дәӢгҖӮеҗҗи•ғжқҫиөһе№Іеёғзҡ„жӣҫеӯҷйғҪжқҫиҠ’еёғжқ°пјҢ继дҪҚеҗҺеҫ—дәҶдёҖеңәйҮҚз—…пјҢиҜ·дәҶеҫҲеӨҡеҗҚеҢ»йғҪжІЎжңүеҢ»жІ»еҘҪгҖӮдёҖеӨ©пјҢд»–жӯЈеңЁзҺӢе®«йҮҢдёҖзӯ№иҺ«еұ•пјҢдёҖеҸӘеҸЈиЎ”з»ҝж ‘жһқзҡ„йЈһйёҹеҒңеңЁзҺӢе®«зҡ„зӘ—еҸ°дёҠгҖӮи—ҸзҺӢеҚҒеҲҶжғҠеҘҮпјҢеҫ…йёҹе„ҝйЈһиө°еҗҺпјҢжҙҫдәәеҸ–жқҘж ‘жһқд»”з»Ҷз«ҜиҜҰпјҢиҘҝи—Ҹй«ҳеҺҹд»ҺжқҘжІЎжңүиҝҷж ·зҡ„ж ‘жһқгҖӮд»–ж‘ҳдёӢдёҖзүҮз»ҝеҸ¶пјҢеҡјеңЁеҳҙйҮҢпјҢж»ЎеҸЈйҶҮйҰҷпјҢз—…д№ҹиҪ»дәҶи®ёеӨҡгҖӮдәҺжҳҜд»–жҙҫеҮәдҪҝиҖ…еӣӣеӨ„еҜ»жүҫиҝҷз§Қе®қж ‘пјҢжңҖз»Ҳиў«дёҖдҪҚеӨ§иҮЈеңЁдёңж–№жұүж—Ҹең°еҢәзҡ„дёҖдёӘз»ҝиүІеҜҶжһ—дёӯжүҫеҲ°дәҶгҖӮеңЁдёҖеҸӘиҒӘжҳҺиҪ»жҚ·зҡ„马й№ҝе’ҢдёҖеҸӘзЁійҮҚзҹ«еҒҘзҡ„еӨ§иұЎзҡ„её®еҠ©дёӢпјҢе°Ҷе®қж ‘иҝҗеӣһйӣӘеҹҹй«ҳеҺҹгҖӮйғҪжқҫиҠ’еёғжқ°зңӢеҲ°зӣҙжҢәжҢәзҡ„ж ‘е№ІгҖҒж·ұз»ҝзҡ„еҸ¶еӯҗпјҢй—®пјҡ“иҝҷеҸ«д»Җд№Ҳж ‘пјҹ”еӨ§иҮЈеӣһзӯ”пјҡ“жұүең°дәәеҸ«ж§ҡпјҢжіЎзқҖе–қиғҪжІ»е°Ҹз—…пјҢз…®зқҖе–қиғҪжІ»еӨ§з—…”гҖӮиҝҷдёӘж•…дәӢи®°иҪҪдәҺ500е№ҙеүҚеҮәзүҲзҡ„и—Ҹж–Үе…ёзұҚгҖҠз”Іеё•дјҠд»“гҖӢдёӯпјҢиҝҷдёҺеҪ“д»ЈиҢ¶еӯҰ家еә„жҷҡиҠізӯүдәәзј–и‘—зҡ„гҖҠйҘ®иҢ¶жј«иҜқгҖӢдёӯзҡ„ж•…дәӢеҚҒеҲҶзӣёдјјгҖӮиҝҷиҜҙжҳҺпјҢиҢ¶еҸ¶жңҖж—©дёҚжҳҜз”ЁжқҘз”ҹжҙҘжӯўжёҙзҡ„йҘ®е“ҒпјҢиҖҢжҳҜз”ЁжқҘжІ»з–—з–ҫз—…зҡ„иүҜиҚҜгҖӮ
е…ғд»ЈпјҢи—Ҹж—Ҹй«ҳеғ§еЎ”е·ҙжқ°дёӯпјҢ30еІҒж—¶пјҢжҖҖзқҖдёҖйў—ж…ҲжӮІд№ӢеҝғпјҢд»ҘжғҠдәәзҡ„жұӮзҹҘж¬ІжңӣпјҢзҰ»ејҖиҘҝи—ҸеүҚеҫҖе·ҙиңҖгҖҒж»ҮеҚ—пјҢдёҖиҫ№жёёи§ҲеҗҚеұұеӨ§е·қгҖҒжңқжӢңдҪӣж•ҷеҗҚеҜәпјҢдёҖиҫ№еӯҰд№ иҖғеҜҹдёҺи—Ҹж°‘ж—ҸжҒҜжҒҜзӣёе…ізҡ„иҢ¶еҸ¶гҖӮд»–зӣ®е…үжіЁи§ҶпјҢеҝғзҒөж„ҹзҹҘпјҢдәІиә«дҪ“йӘҢпјҢжҺҢжҸЎдәҶеӨ§йҮҸжңүе…іиҢ¶еҸ¶зҡ„第дёҖжүӢиө„ж–ҷгҖӮ40еІҒеҗҺиҝ”еӣһиҘҝи—ҸпјҢж’°еҶҷдәҶи—Ҹж—Ҹ第дёҖйғЁиҢ¶з»ҸгҖҠз”ҳйңІд№Ӣжө·гҖӢгҖӮд№ҰдёӯиҜҰе°Ҫе·§еҰҷең°д»Ӣз»ҚдәҶиҢ¶д№Ӣзұ»гҖҒиҢ¶д№Ӣе…·гҖҒиҢ¶д№Ӣзғ№гҖҒиҢ¶д№ӢзӨјгҖҒиҢ¶д№ӢзӣҠпјҢе’ҢйҷҶзҫҪзҡ„гҖҠиҢ¶з»ҸгҖӢжңүи®ёеӨҡдёҚи°ӢиҖҢеҗҲеӨ„пјҢжҳҜеҸӨд»Ји—Ҹж—Ҹдј ж’ӯе’ҢеҸ‘еұ•иҢ¶ж–ҮеҢ–зҡ„жқғеЁҒи‘—дҪңгҖӮ
пјҲдәҢпјү
иңҖж»ҮжҳҜиҢ¶зҡ„еҸ‘жәҗең°гҖҒз”ҹдә§ең°пјҢдёҺиҘҝи—Ҹзӣёйҡ”еҚғдёҮйҮҢгҖӮдҪҶеҚғеұұдёҮж°ҙгҖҒиү°йҡҫйҷ©йҳ»жҢЎдёҚдҪҸеҮ иҝ‘зӢӮзғӯзҡ„йңҖжұӮпјҢиў«з§°дёәй»‘иүІй»„йҮ‘зҡ„иҢ¶еҸ¶пјҢд»Һе·қж»ҮжәҗжәҗдёҚж–ӯең°иҝӣе…Ҙйқ’и—Ҹй«ҳеҺҹгҖӮ
еҺҶеҸІдёҠпјҢдёӯеӨ®зҺӢжңқжңҖеҲқжҙҫеҫҖжӢүиҗЁзҡ„е®ҳе‘ҳпјҢйҰҲиө зӨје“ҒеӨҡж•°жҳҜиҢ¶еҸ¶пјҢиҢ¶жҲҗдәҶдёҚеҸҜеӨҡеҫ—зҡ„зЁҖдё–зҸҚе“ҒгҖӮйҡҸзқҖдёӯеҺҹең°еҢәеҜ№й©¬еҢ№йңҖжұӮзҡ„еўһеӨ§пјҢеҮәзҺ°дәҶ“иҢ¶й©¬дә’еёӮ”пјҢи—Ҹж—Ҹдәәиө¶зқҖеӨ§жү№й©¬зҫӨпјҢеҲ°иҫ№е·һдәӨжҚўиҢ¶еҸ¶гҖӮеҗҺжқҘпјҢеҲҶж•Јзҡ„иҙёжҳ“ж–№ејҸиў«е®ҳеәңз»ҹз®Ўиө·жқҘпјҢеҲҶеҲ«еңЁе…°е·һгҖҒйӣ…е®үзӯүең°пјҢи®ҫзҪ®дәҶеҚҒеҮ дёӘиҢ¶й©¬дәӨжҳ“дёӯеҝғпјҢеҜ№иҢ¶й©¬д»·жҜ”гҖҒдәӨжҳ“ж•°йҮҸе®һиЎҢз»ҹдёҖз®ЎеҲ¶гҖӮ
е·қиҢ¶жңҖж—©иҝӣе…ҘиҘҝи—Ҹеҗ„ең°гҖӮеҪ“ж—¶иҢ¶й©¬дәӨжҳ“дёӯеҝғзҡ„иҢ¶еҹәжң¬жҳҜиңҖиҢ¶пјҢйҡҸзқҖе·қиңҖиҢ¶еҸ¶дёҚж–ӯиҝҗжқҘпјҢеӮЁеӨҮиҢ¶зҡ„д»“еә“дёҚж–ӯжү©е»әпјҢиҢ¶й©¬дәӨжҚўзҡ„规模дёҚж–ӯжү©еӨ§пјҢиҢ¶еҸ¶д»ҺиҘҝи—ҸзҺӢе…¬иҙөж—Ҹзҡ„зӢ¬дә«йҘ®е“ҒпјҢжү©еұ•еҲ°жҷ®йҖҡеӨ§дј—зҡ„е–ңзҲұд№Ӣзү©гҖӮдёӯеӨ®ж”ҝеәңйҡҸд№ӢеҠ ејәеҜ№иҘҝи—Ҹзҡ„з®ЎзҗҶпјҢи—ҸеҢәзҡ„е®—ж•ҷйўҶиў–гҖҒеңҹеҸёеӨҙдәәзә·зә·е…Ҙжңқи§җи§ҒпјҢжҺҲе®ҳиҒҢе°ҒзҲөдҪҚпјҢ他们иҝӣиҙЎй©¬еҢ№д№ӢеӨ–пјҢиҝҳжңүзәўиҠұгҖҒйәқйҰҷгҖҒж°Ҷж°Үзӯүеңҹзү№дә§е“ҒпјҢеҫ—еҲ°зҡ„иөҸиөҗе“ҒйҷӨиҢ¶еҸ¶д№ӢеӨ–иҝҳжңүй”ҰзјҺгҖҒдёқз»ёгҖҒз“·еҷЁпјҢиҺ·еҫ—зҡ„еӨ§еӨ§еӨҡдәҺиҝӣиҙЎзҡ„гҖӮ他们е°ҶдёҚдҫҝжҗәеёҰиҝҗиҫ“зҡ„зү©е“ҒеңЁеёӮеңәдәӨжҚўжҲҗиҢ¶еҸ¶пјҢжңқиҙЎдә’еёӮеҸҳдёәиҢ¶й©¬дә’еёӮзҡ„еҸҰдёҖз§ҚеҪўејҸпјҢе·©еӣәдәҶиҘҝи—Ҹең°ж–№е’ҢдёӯеӨ®ж”ҝеәңзҡ„иҮЈеұһе…ізі»гҖӮ
ж»Үе·қзҡ„иҢ¶е•ҶзңӢеҲ°дәҶиҘҝи—Ҹзҡ„иҢ¶еҸ¶еёӮеңәпјҢдё“й—ЁеҲ¶дҪңдәҶиҝҗиҫ“ж–№дҫҝгҖҒеҪўзҠ¶иҖҗзңӢгҖҒе“ҒиҙЁеҲҶзә§зҡ„иҢ¶еҸ¶пјҢеҸ–еҗҚеҸ«“иҫ№иҢ¶”пјҢ жҠҠиҢ¶еҸ¶еӣӨз§ҜеҲ°еӣәе®ҡеёӮеңәпјҢеҚ•зәҜзҡ„иҢ¶й©¬дәӨжҳ“еҸҳжҲҗдәҶиҫ№иҢ¶иҙёжҳ“гҖӮеҗҺжқҘпјҢиҘҝи—ҸеӨ§зҡ„еҜәйҷўгҖҒиҙөж—ҸгҖҒе•ҶжҲ·пјҢз»„з»Үиө·еәһеӨ§зҡ„йӘЎй©¬иҝҗиҫ“йҳҹпјҢи¶ҠиҝҮз§ҜйӣӘзҡ„й«ҳеұұгҖҒж№ҚжҖҘзҡ„жұҹжІіпјҢеңЁдё–з•ҢжңҖиү°йҡҫзҡ„и·ҜйҖ”дёҠй•ҝйҖ”и·Ӣж¶үпјҢжҠҠиҢ¶еҸ¶иҝҗеӣһиҘҝи—ҸгҖӮе…ғжҳҺжё…дёүжңқеҪўжҲҗдәҶд»Һж»Үе·қеҲ°иҘҝи—Ҹзҡ„“иҢ¶дёҡд№Ӣи·Ҝ”“иҢ¶й©¬д№Ӣи·Ҝ”“иҢ¶й©¬еҸӨйҒ“”зӯүеӨҡжқЎиҙёжҳ“йҖҡйҒ“гҖӮиҢ¶й©¬иҙёжҳ“е…ҙзӣӣж—¶пјҢд»…д»ҺжӢүиҗЁеҲ°йӣ…е®үзҡ„е•ҶйҳҹпјҢжҜҸе№ҙи—ҸеҺҶдёүжңҲеҮәеҸ‘пјҢе°‘еҲҷзҷҫдәәеҚғеҢ№йӘЎй©¬пјҢеӨҡеҲҷеҚғдәәдёҮеҢ№йӘЎй©¬пјҢжө©жө©иҚЎиҚЎпјҢйЈҺйӣЁж— йҳ»пјҢйҳІзқҖзӣ—еҢӘпјҢйЈҺйӨҗйңІе®ҝпјҢж—ҘеӨҚдёҖж—ҘпјҢе№ҙеӨҚдёҖе№ҙпјҢдёҖи¶ҹжқҘеӣһзәҰдёҖе№ҙжңүдҪҷгҖӮеҶ…ең°е•ҶдәәпјҢд№ҹзңӢдёҠдәҶи—Ҹең°иҚҜжқҗгҖҒзҡ®жҜӣгҖҒ马еҢ№зӯүзү№дә§пјҢж“…й•ҝз»Ҹе•Ҷзҡ„ж»Үдәәиө¶зқҖ马帮жҠҠиҢ¶гҖҒзі–гҖҒй“ңеҷЁпјҢиҝҗеҲ°жӢүиҗЁпјҢеӣ еҫҖиҝ”и·ҜйҖ”еӨӘиҝңпјҢе°ұеңЁиҘҝи—Ҹз§ҹе•Ҷй“әгҖҒе»әе®ўж ҲгҖӮж»ҮиҢ¶жңүжӮ д№…зҡ„еҺҶеҸІпјҢиҢ¶иҙЁеҫ—еӨ©зӢ¬еҺҡпјҢдҪҶзғҳз„ҷжҠҖжңҜиҫғе·®пјҢдёҪжұҹзҡ„жңЁж°ҸеңҹеҸёпјҢзҹҘйҒ“зәіиҘҝж—Ҹе’Ңи—Ҹж—ҸеҗҢжңүе—ңиҢ¶зҡ„д№ дҝ—пјҢеңЁж»Үи—ҸжҺҘеЈӨзҡ„ж°ёиғңгҖҒз»ҙиҘҝе»әз«ӢдәҶиҢ¶й©¬дә’еёӮиҙёжҳ“еёӮеңәпјҢйј“еҠұе•ҶдәәеҲ°иҘҝи—Ҹз»ҸиҗҘиҢ¶еҸ¶гҖӮ
жё…еҲқпјҢзәіиҘҝж—Ҹе•ҶдәәжқҺжӮҰз»ҸиҗҘд»ҘиҢ¶еҸ¶дёәдё»зҡ„ж»Үи—Ҹиҙёжҳ“пјҢжҲҗдёәи‘—еҗҚеҜҢе•ҶпјҢжё…жң«ж»ҮиҢ¶еңЁиҘҝи—Ҹзҡ„й”ҖйҮҸи¶…иҝҮе·қиҢ¶пјҢеҪ“ж—¶жқҘеҫҖдәҺдёҪжұҹе’ҢжӢүиҗЁзҡ„и—Ҹж—Ҹе•Ҷдәә马帮1дёҮеӨҡеҢ№пјҢеҸҢзЁӢиҝҗйҮҸзәҰ2000еҗЁгҖӮеҸҜд»ҘиҜҙпјҢиҢ¶жҳҜи—ҸжұүеҸӢи°Ҡзҡ„зәҪеёҰпјҢд№ҹжҳҜи—Ҹжұүеӣўз»“зҡ„иұЎеҫҒгҖӮиҝ‘д»ЈпјҢиӢұеӣҪеңЁиҝһз»ӯе…ҘдҫөиҘҝи—Ҹж—¶пјҢзңӢеҲ°иҢ¶жҳҜжұүи—ҸзҰ»дёҚејҖзҡ„еӣ зҙ д№ӢдёҖпјҢзӯ–еҲ’дәҶеҚ°иҢ¶е…Ҙи—Ҹзҡ„йҳҙи°ӢгҖӮ他们д»ҘжҺўйҷ©е®¶зҡ„еҗҚд№үз»„з»ҮдәҶ马йҳҹпјҢжҠҠеҚ°иҢ¶д»ҺеҚ°еәҰзҡ„еӨ§еҗүеІӯиҝҗеҲ°жӢүиҗЁпјҢйҖ”з»Ҹй”ЎйҮ‘гҖҒдәҡдёңпјҢеҸӘжңүеҚҒеӨҡеӨ©зҡ„и·ҜзЁӢгҖӮдјҒеӣҫз”ЁеҚ°иҢ¶еһ„ж–ӯиҘҝи—ҸеёӮеңәпјҢжҲӘж–ӯиҘҝи—ҸдёҺеҶ…ең°зҡ„иҒ”зі»гҖӮеҚ°иҢ¶жҖ§зғӯиӢҰ涩пјҢиүІжіҪеҸҲй»‘еҸҲжө“пјҢеҲ¶дҪңжқҫиҪҜжҳ“зўҺгҖӮи—Ҹж—Ҹе®Ғж„ҝиҲҚиҝ‘жұӮиҝңпјҢеҶҚзҙҜеҶҚиӢҰд№ҹиҰҒиө¶зқҖ马帮еҲ°еҶ…ең°й©®еӣһжұүиҢ¶гҖӮ
пјҲдёүпјү
йӣӘеҹҹй«ҳеҺҹпјҢе·ҚеіЁеЈ®дёҪпјҢж°”е®ҮиҪ©жҳӮпјҢжҳҜиӢҚз©№дёӢзҡ„еҮҖеңҹпјҢжҳҜеӨ§ең°дёҠзҡ„дё°зў‘пјҢд»Өдәәж— йҷҗзҘһеҫҖ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иҰҒеңЁиҝҷең°еҠҝй«ҳеі»гҖҒж°”еҖҷеҜ’еҶ·гҖҒз©әж°”зЁҖи–„зҡ„ең°ж–№пјҢз”ҹеӯҳгҖҒз”ҹжҙ»гҖҒз№ҒиЎҚпјҢдёҖиҰҒжңүжҠөеҫЎй«ҳеҜ’зјәж°§зҡ„иә«дҪ“зҙ иҙЁпјҢдәҢиҰҒжңүиҝҺжҺҘиҮӘ然йЈҺйҷ©зҡ„з”ҹжҙ»жҷәж…§гҖӮи—Ҹж—Ҹж°‘и°Јпјҡ“иҢ¶жҳҜе‘ҪпјҢиҢ¶жҳҜиЎҖ”пјҢ“дәәдәәзҰ»дёҚејҖиҢ¶пјҢеӨ©еӨ©зҰ»дёҚејҖиҢ¶”пјҢйҒ“еҮәдәҶз”ҹжҒҜеңЁй«ҳеҺҹдёҠзҡ„и—Ҹж—ҸеҜ№иҢ¶зҡ„йңҖжұӮгҖӮ
иҫҪйҳ”зҫҺдёҪзҡ„и—ҸеҢ—иҚүеҺҹпјҢжө·жӢ”4500зұіпјҢз”ҹжҙ»еңЁиҝҷйҮҢзҡ„и—Ҹж°‘пјҢдҫқйқ еӨ©з„¶зү§еңәйҖҗж°ҙиҚүиҖҢеұ…гҖӮ他们з”ҹдә§зҡ„жҳҜй«ҳи„ӮиӮӘгҖҒй«ҳиӣӢзҷҪзҡ„зүӣзҫҠиӮүгҖҒеҘ¶еҲ¶е“ҒпјҢз”ҹжҙ»дёӯеҝ…йЎ»йқ иҢ¶и§Ји…»гҖҒеҠ©ж¶ҲеҢ–гҖӮжІҹеЈ‘зәөжЁӘзҡ„и—ҸеҚ—и°·ең°пјҢжӣҫжҳҜиҘҝи—ҸеҶңдёҡж–ҮжҳҺзҡ„еҸ‘зҘҘең°пјҢжө·жӢ”3400зұіпјҢ他们з§ҚжӨҚй«ҳеҺҹзү№жңүзҡ„йқ’зЁһпјҢз”ұйқ’зЁһеҠ е·Ҙзҡ„зіҢзІ‘жҳҜ他们зҡ„дё»йЈҹгҖӮзіҢзІ‘ж— и®әжҖҺд№ҲйЈҹз”ЁпјҢйғҪзҰ»дёҚејҖиҢ¶ж°ҙзӣёдјҙгҖӮеңЁиҘҝи—ҸпјҢзіҢзІ‘гҖҒй…ҘжІ№гҖҒзүӣзҫҠиӮүе’ҢиҢ¶еҸ¶жҳҜйҘ®йЈҹзҡ„еӣӣиҰҒзҙ пјҢд№ҹжҳҜз”ҹжҙ»зҡ„еӣӣиҰҒзҙ гҖӮ
и—Ҹж°‘ж—ҸжҠҠз”ҹеӯҳеҪ“еҒҡж–ҮеҢ–пјҢжҠҠз”ҹжҙ»еҪ“дҪңиүәжңҜгҖӮи—Ҹж—Ҹж–ҮеҢ–иЎЁзҺ°еңЁиһҚе…ҘеҶ…еҝғзҡ„дҝ®е…»гҖҒж— йңҖжҸҗйҶ’зҡ„иҮӘи§үгҖҒзәҰжқҹиЎҢдёәзҡ„иҮӘз”ұгҖҒе…»жҲҗд№ жғҜзҡ„е–„иүҜпјҢеңЁж—ҘеёёиЎЁзҺ°еҮәжқҘзҡ„жҳҜиұӘж”ҫгҖҒиҜҡе®һгҖҒзғӯжғ…гҖӮйЈҺжғ…д№ дҝ—жҳҜж°‘ж—Ҹж–ҮеҢ–зҡ„ж ҮиҜҶе’ҢеҫҪи®°пјҢиҘҝи—ҸиҢ¶ж–ҮеҢ–жҠҳе°„еҮәж°‘ж—Ҹз”ҹеӯҳз№ҒиЎҚдёӯзҡ„еҝғзҗҶгҖҒжҖ§ж је’ҢйЈҺжғ…зү№еҫҒгҖӮ
и—Ҹиғһ家еҰӮжһңиҝӣжқҘдёҖдёӘйҷҢз”ҹдәәпјҢйҰ–е…Ҳ敬дҪ дёҖжқҜиүІжіҪж·Ўй»„гҖҒйҰҷж°”жү‘йј»зҡ„й…ҘжІ№иҢ¶пјӣеҰӮжһңдҪ жҳҜжқҘеҒҡе®ўпјҢиҝҳиҰҒз»ҷдҪ зҢ®дёҠдёҖжқЎжҙҒзҷҪзҡ„е“ҲиҫҫгҖӮдәІеҸӢеҮәй—ЁиҝңиЎҢпјҢдёҖ家дәәжҲ–е…Ёжқ‘дәәжҸҗзқҖй…ҘжІ№иҢ¶еүҚжқҘйҖҒиЎҢпјҢзҢ®дёҠдёҖжқЎе“ҲиҫҫпјҢе–қдёҠдёүжқҜй…ҘжІ№иҢ¶пјҢдёҖи·ҜеҗүзҘҘеҰӮж„ҸгҖӮе©ҡ姻дёӯд»Һ男方家жҸҗдәІгҖҒжӢ©ж—Ҙи®ўе©ҡпјҢеҲ°иҝҺжҺҘж–°еЁҳгҖҒдёҫиЎҢе©ҡзӨјпјҢзјәдәҶиҢ¶й…’е“ҲиҫҫдёҖдәӢж— жҲҗгҖӮиө·еұ…зӨјдҝ—дёӯпјҢе»әжҲҝеҘ еҹәпјҢз ҙеңҹеҠЁе·ҘпјҢдёҠжўҒз«ӢжҹұпјҢе°ҒйЎ¶з«Је·ҘпјҢд№”иҝҒд№Ӣе–ңпјҢиҢ¶й…’е“ҲиҫҫжҳҜеҝ…йЎ»зҡ„зү©е“ҒгҖӮж–°иө·зҒ¶пјҢзӮ№зҒ«з…®зҡ„第дёҖй”…жҳҜиҢ¶пјӣжҗ¬ж–°жҲҝпјҢе…Ҳе…ҘеұӢзҡ„第дёҖ件зү©е“ҒжҳҜиҢ¶пјӣжұӮиҙөдәәеё®еҝҷпјҢиҰҒйҖҒзҡ„зӨјзү©йҰ–йҖүжҳҜиҢ¶пјӣжҜҸйҖўи—ҸеҺҶж–°е№ҙпјҢеңЁдҪӣйҫӣеүҚж‘Ҷж”ҫзҡ„жҳҜиҢ¶гҖҒзӣҗе’Ңй…ҘжІ№гҖӮ
и—Ҹж—ҸиҝҳжҠҠиҢ¶еҸ¶еҪ“дҪңеңЈзү©пјҢж–°еЎ‘зҡ„дҪӣеғҸпјҢиЈ…и—Ҹж—¶йҷӨдәҶйҮ‘银зҸ е®қгҖҒдә”и°·еңЈзү©пјҢиҝҳеҝ…йЎ»жңүиҢ¶пјӣи—Ҹ民家йҮҢзҡ„з§ҜзҰҸз®ұпјҢйҷӨдәҶ家ж—ҸеҺҶеҸІзӣёдј зҡ„е®қзү©пјҢиҝҳиҰҒиЈ…дёҠдёҖеқ—иҢ¶еҸ¶гҖӮи—Ҹж—ҸжҠҠиҢ¶е’ҢзӣҗжҜ”е–»дёәеҸӢи°Ҡе’ҢзҲұжғ…зҡ„иұЎеҫҒпјҢжңүдёҖйҰ–жӯҢе”ұйҒ“пјҡ“жқҘиҮӘжұүең°зҡ„иҢ¶пјҢжқҘиҮӘи—ҸеҢ—зҡ„зӣҗпјҢеңЁй…ҘжІ№жЎ¶еҶ…зӣёиҒҡпјҢиһҚеҗҲиҖҢжҲҗзҡ„й…ҘжІ№иҢ¶пјҢиҠійҰҷеҸҲз”ңиңңпјҢйӮЈжҳҜеңҶж»ЎдҝұдҪізҡ„姻зјҳгҖӮ”300е№ҙеүҚпјҢдёҖдҪҚй«ҳеғ§еҶҷдәҶдёҖзҜҮйўӮиҢ¶иҜҚпјҡ“иҢ¶жҳҜдәәзұ»зҡ„ж•‘жҳҹпјҢд»ҘиҠӮзңҒиҮӘе·ұзҡ„ж—¶й—ҙпјҢ延й•ҝдәәзҡ„з”ҹе‘ҪпјҢдәәдёҺдәәзӣёдә’з…§йЎҫпјҢиҢ¶дёҺж°ҙйңҖиҰҒиһҚеҗҲпјҢжңҖеҘҪзҡ„ж°ҙеңЁжңҖй«ҳеӨ„пјҢиҢ¶еҸ¶и¶ҠиҝҮеҚғдёҮеұұпјҢиҰҒдёҺзў§ж°ҙз»“зјҳеҲҶгҖӮ”еңЁиҚүеҺҹж”ҫзү§зҡ„пјҢз”°йҮҺйҮҢиҖ•з§Қзҡ„пјҢе•ҶйҒ“дёҠиө¶й©¬зҡ„пјҢеұұи·ҜдёҠжңқдҪӣзҡ„пјҢеҲ°дәҶеҚҲж—¶пјҢжҗ¬жқҘдёүеқ—зҹіеӨҙпјҢж”Ҝиө·еӨ§е°ҸиҢ¶й”…пјҢиҲҖдёҠжё…жіүжәӘж°ҙпјҢз…Ҫиө·зҡ®йЈҺиўӢпјҢиҢ¶ж°”йЈҳеӣӣж–№пјҢдәә们ејҖе§ӢеӣҙзқҖиҢ¶й”…еёӯең°иҖҢеқҗпјҢи°Ҳ笑йЈҺз”ҹгҖӮиҝҷжҳҜдёҖйҒ“дә®дёҪзҡ„й«ҳеҺҹйЈҺжҷҜпјҢж— дёҚжё—йҖҸзқҖиҢ¶ж–ҮеҢ–зҡ„зІҫзҘһдә«еҸ—пјҢеҚідҫҝиҝҷз§Қз®Җжҳ“зҡ„зҶ¬иҢ¶пјҢе®ғзҡ„ж°ҙжәҗйҖүжӢ©гҖҒз…®иҢ¶зҒ«еҖҷгҖҒзҹізҒ¶ж–№дҪҚйғҪжҳҜзІҫеҝғзӯ№еҲ’иҝҮзҡ„гҖӮиҝҷж—¶з…®иҢ¶и®Із©¶зҡ„жҳҜзҒ«еҖҷиҰҒеӨҹпјҢжҹҙзғҹиҰҒй«ҳпјҢиҢ¶жІ«иҰҒи¶іпјҢиҢ¶ж°”иҰҒжө“гҖӮ
пјҲеӣӣпјү
и—Ҹж—ҸдәәйҷӨдәҶзҷҪеӨ©йӘ‘еңЁй©¬дёҠгҖҒеӨңйҮҢзқЎеңЁеәҠдёҠд№ӢеӨ–пјҢйғҪе’ҢиҢ¶еңЁдёҖиө·гҖӮд»ҺеӨ–ең°еҲ°иҘҝи—Ҹж—…иЎҢзҡ„дәәпјҢж— и®әеңЁеҶңжқ‘гҖҒзү§еҢәжҲ–еҹҺй•ҮпјҢйҡҸеӨ„йғҪиғҪзңӢеҲ°иҢ¶зҡ„иә«еҪұгҖҒй—»еҲ°иҢ¶зҡ„йЈҳйҰҷгҖӮйҷӨдәҶй…ҘжІ№иҢ¶пјҢеҹҺй•ҮжңҖзӣӣиЎҢзҡ„жҳҜз”ңиҢ¶гҖӮй”…йҮҢз…®дёҠзәўиҢ¶зІүпјҢиҰҒзңӢиүІжіҪеҸҳйҮ‘й»„пјҢеҠ иҝӣзүӣеҘ¶зңӢжө“еәҰпјҢдёҚзЁ дёҚж·ЎеҶҚеҠ зі–гҖӮдёҠдё–зәӘ80е№ҙд»ЈеҲқпјҢжӢүиҗЁдәәеҸЈдёҚеҲ°5дёҮпјҢеҹҺйҮҢзҡ„з”ңиҢ¶йҰҶе°ұжңү100еӨҡ家пјҢиҝӣдәҶиҢ¶е®ӨпјҢдәәдәәдёҖеҫӢе№ізӯүгҖӮиҝҷйҮҢзҡ„е®ўдәәе–қиҢ¶пјҢеҘҪеғҸиҜ»иҜ—гҖҒе“Ғз”»пјҢеҸҲеғҸжҳҜи°ҲеҝғгҖҒиҫ©и®әгҖӮиҝҷйҮҢжҳҜж–°й—»дёӯеҝғпјҢеӣҪдәӢ家дәӢпјҢдё–жҖҒдәәз”ҹпјҢжӯЈеҸІйҮҺеҸІпјҢжӮІж¬ўзҰ»еҗҲпјӣиҝҷйҮҢеҸҲжҳҜдәӨжҳ“дёӯеҝғпјҢеҜҹиҙ§йӘҢиҙ§пјҢи®Ёд»·иҝҳд»·пјҢзҺ©з¬‘йҖ—д№җпјҢж— жӢҳж— жқҹгҖӮйӮ»йҮҢдёҚе’ҢзқҰпјҢжңӢеҸӢжңүйҡ”йҳӮпјҢеҲ°иҢ¶йҰҶе–қдёҠеҚҠеӨ©иҢ¶пјҢд»ҮжҖЁзғҹж¶Ҳдә‘ж•ЈпјҢйҮҚеҪ’дәҺеҘҪпјҢжҸЎжүӢиЁҖж¬ўгҖӮжңүеҸҘеҸӨиҜқпјҡдёҚиғҪ敬жҲ‘д»ҘиҢ¶пјҢиҝҳд№Ӣд»Ҙж°ҙгҖӮ
“иғҪиЎҢеҚғйҮҢзҡ„еҘҪ马пјҢеҝ…йЎ»й…ҚдёҠйҮ‘йһҚпјҢжқҘиҮӘжұүең°зҡ„еҘҪиҢ¶пјҢеҝ…йЎ»зӣӣеңЁзҺүзў—гҖӮ”и—Ҹж—ҸдәәйҷӨдәҶдҪҸжҲҝпјҢжңҖ讲究зҡ„жҳҜиҢ¶е…·пјҢиҢ¶й”…иҢ¶жЎ¶пјҢиҢ¶еЈ¶иҢ¶зў—пјҢеҸ·з§°еӣӣеӨ§иҢ¶е…·гҖӮйҖ еһӢзҫҺи§Ӯзҡ„й“ңй”…пјҢиҪ»е·§ж–№дҫҝзҡ„й“қй”…пјҢзІҫиҮҙе…үдә®зҡ„йҷ¶й”…пјҢзҶ¬еҮәйҶҮйҰҷзҡ„жё…иҢ¶гҖӮ
жңҖе°Ҹзҡ„й“қй”…иғҪиЈ…дёҖеҚҮж°ҙпјҢз…®еҮәзҡ„иҢ¶еӨҹдёӨдёӘдәәе–қгҖӮжңҖеӨ§зҡ„й“ңй”…еҸЈеҫ„дёӨзұіе®ҪпјҢж·ұеәҰ1.8зұіпјҢзҶҠзҶҠзҒ«з„°зғ§ејҖж»ҡзғ«зҡ„ејҖж°ҙпјҢеҚҒеӨҡж–Өзҡ„з –иҢ¶ж”ҫе…Ҙж°ҙдёӯпјҢзҶ¬жҲҗзҗҘзҸҖиүІзҡ„иҢ¶жұӨпјҢеҸҜдҫӣеҚғдәәйҘ®з”ЁгҖӮжҚ®дј°и®ЎпјҢиҝҷж ·зҡ„иҢ¶й”…еңЁиҘҝи—Ҹзҡ„е“ІиҡҢеҜәгҖҒиүІжӢүеҜәгҖҒз”ҳдё№еҜәе’Ңйқ’жө·зҡ„еЎ”е°”еҜәпјҢжңүж•°еҚҒдёӘгҖӮиҢ¶жЎ¶жҳҜй…ҘжІ№иҢ¶зҡ„еҠ е·Ҙе·Ҙе…·пјҢиҢ¶жұӨгҖҒй…ҘжІ№еңЁжЎ¶еҶ…жҗ…жӢҢиҖҢжҲҗй…ҘжІ№иҢ¶гҖӮзәўжЎҰжңЁгҖҒйқ’ж —жңЁгҖҒж ёжЎғжңЁжҳҜеҲ¶дҪңиҢ¶жЎ¶зҡ„йҰ–йҖүжқҗж–ҷпјҢдёҚжҳ“ејҖиЈӮпјҢйҖӮеҗҲеҪ“ең°е№ІзҮҘзҡ„ж°”еҖҷгҖӮи—ҸеҢ—жҷ®йҖҡзү§ж°‘家дҪҝз”Ёзҡ„еёёеёёжҳҜз®Җжҳ“зҡ„з«№зӯ’пјҢзІ—еЈ®зҡ„дё»е№ІпјҢжү“йҖҡз«№иҠӮдҫҝиғҪжҲҗдёәй…ҘжІ№жЎ¶гҖӮиҮідәҺиҢ¶еЈ¶иҢ¶зў—пјҢжңҖй«ҳжЎЈзҡ„жҳҜйҮ‘жқҜ银壶гҖҒ银жқҜйҮ‘еЈ¶пјҢжҷ®йҖҡзҡ„жҳҜй“ңеЈ¶й“қеЈ¶гҖҒзҺү碗瓷瓶гҖӮжҲ‘еңЁеёғиҫҫжӢүе®«зңӢеҲ°зҡ„жңҖж—©зҡ„з“·иҢ¶зў—еӣҫжЎҲжҳҜпјҡйёҹе„ҝиЎ”иҢ¶гҖҒйҮ‘й№ҝиғҢиҢ¶гҖҒй•ҝеҜҝзҪ—жұүгҖӮи—Ҹең°жңҖжҷ®йҖҡзҡ„иҢ¶е…·жҳҜжңЁзў—гҖӮи—Ҹж—Ҹдәәе–қиҢ¶пјҢжңҖ讲究зҡ„жҳҜеӨ«еҰ»дёҚе…ұзў—пјҢеӯҗеҘідёҚе…ұзў—пјҢжҜҸдәәдёҖдёӘжңЁзў—пјҢдәәиө°зў—йҡҸпјҢеҪўеҪұдёҚзҰ»гҖӮзҷҫе№ҙеүҚпјҢдёҠиҮіе®ҳз•ҢиҰҒдәәпјҢдёӢиҮіиЎ—еӨҙд№һдёҗпјҢйғҪйҡҸиә«еёҰзқҖе–қиҢ¶зҡ„жңЁзў—гҖӮжӢүиҗЁзҡ„иҫҫе®ҳжҳҫиҙөи…°дёҠжҢӮзқҖдёӨж ·зү©е“ҒпјҢдёҖиҫ№жҳҜзў—пјҢз”ЁжқҘе–қиҢ¶зҡ„пјӣдёҖиҫ№жҳҜе°ҸеҲҖпјҢз”ЁжқҘеҗғиӮүзҡ„гҖӮзјҺеҲ¶зҡ„зў—еҘ—д»Һдёғе“ҒеҲ°дёүе“ҒејҸж ·дёҚеҗҢгҖҒеҒҡе·ҘдёҚеҗҢпјҢд»Һзў—еҘ—еҸҜд»ҘиҜҶеҲ«е®ҳйҳ¶пјҢжҜҸж¬ЎејҖдјҡжҲ–еҠһе…¬пјҢдёҚз®ЎжҖҘдәӢзј“жғ…пјҢйҰ–е…ҲдёҚж…ҢдёҚеҝҷең°д»ҺиҮӘе·ұзҡ„зў—еҘ—йҮҢжӢҝеҮәжңЁзў—пјҢд»Һд»Һе®№е®№ең°е–қдёҠдёүзў—й…ҘжІ№иҢ¶гҖӮ
жӢүиҗЁеӣӣе‘Ёзҡ„еӨ§еҜәйҷўпјҢеҗ„иҮӘзҡ„иҢ¶зў—еҪўзҠ¶д№ҹдёҚзӣёеҗҢпјҢе“ІиҡҢеҜәзҡ„жҳҜй’өејҸиҢ¶зў—пјҢз”ҳдё№еҜәзҡ„жҳҜжўҜејҸиҢ¶зў—пјҢиӢҚеҸӨ尼姑еҜәзҡ„жҳҜе№іеә•иҢ¶зў—пјҢзңӢиҢ¶зў—е°ұзҹҘйҒ“жҳҜе“ӘдёӘеҜәзҡ„еғ§дәәгҖӮдјҙйҡҸзқҖи—Ҹең°йҘ®иҢ¶зҡ„еҺҶеҸІиҝӣзЁӢпјҢйҘ®з”ЁдёҚзғ«еҳҙгҖҒзӣӣиҢ¶дёҚеҸҳе‘ізҡ„жңЁзў—пјҢжҲҗдёәеӨ–еҮәж—¶зҡ„еҝ…еӨҮд№Ӣзү©гҖӮзҺ°еңЁжңЁзў—зҡ„еҲ¶дҪңи¶ҠжқҘи¶ҠзІҫзҫҺпјҢејҸж ·и¶ҠжқҘи¶ҠеҚҺдёҪпјҢжҺЁеҠЁдәҶиҘҝи—Ҹе·Ҙиүәе“Ғзҡ„еҸ‘еұ•гҖӮдёҖдәӣи—Ҹж—Ҹзҡ„иҜҙе”ұиүәдәәпјҢд№ҹжңүиҮӘе·ұдё“з”Ёзҡ„жңЁеҲ¶иҢ¶зў—пјҢе°Ҹзҡ„еӨ§еҰӮзҫҠеӨҙпјҢеӨ§зҡ„еҮ д№Һе’ҢзүӣеӨҙзӣёзӯүпјҢдёҖдёӘдә”зЈ…зғӯж°ҙ瓶зҡ„й…ҘжІ№иҢ¶е…ЁеҖ’иҝӣеҺ»иҝҳиЈ…дёҚж»ЎгҖӮиҝ‘д»ЈиҘҝи—ҸжңҖеҘҪзҡ„жңЁзў—жқҘиҮӘи—ҸеҚ—жҺӘйӮЈиҫҫж—әй•ҮпјҢйӮЈжңЁзў—и–„еҰӮз“·зў—пјҢиҪ»еҰӮзәёжқҜпјҢз»өеҰӮи–„й“қпјҢжҳҜз”ЁзЎ•еӨ§зҡ„ж ‘зҳӨжҠӣе…үжү“зЈЁеҒҡеҮәжқҘзҡ„пјҢзңӢжңЁеӨҙзҡ„зә№и·ҜиғҪеҲҶеҮәжңЁзў—зӯүзә§пјҢеҪ“е№ҙдёҖдёӘзҢ«зңјзә№гҖҒзЈ·зҒ«зә№зҡ„жңЁзў—д»·еҖјдёғе…«еӨҙзүҰзүӣгҖӮж–°з”ҹе„ҝиө·еҗҚд№ӢеҗҺпјҢиҖҒдәәе°ұйҖҒдёҖдёӘжңЁзў—е–қиҢ¶з”ЁпјӣиҖҒдәәеҮҢжҷЁиө·еәҠпјҢдё»еҰҮжҠҠзӣӣж»Ўй…ҘжІ№иҢ¶зҡ„жңЁзў—з«ҜеҲ°еәҠеүҚпјӣиҖҒдәәзҰ»ејҖдәәдё–пјҢ家дәәжҠҠд»–зӣӣж»ЎиҢ¶еҸ¶е’ҢйЈҹе“Ғзҡ„жңЁзў—жҠӣиҝӣжұҹжІігҖӮ
жҲ‘еңЁдә‘еҚ—е·Із»Ҹз”ҹжҙ»дәҶ16е№ҙпјҢд»Ҙиҷ”иҜҡзҡ„еҝғжңқи§җиҝҮе…ӯеӨ§иҢ¶еұұгҖӮеҸӨиҖҒзҡ„иҢ¶ж ‘дёҖеҲ°жҳҘеӨ©пјҢз№ҒиҢӮзқҖиҮӘе·ұйқ’жҳҘзҡ„жһқеҸ¶пјҢиҢӮеҸ¶йЈҺеЈ°з‘ҹз‘ҹпјҢзҙ§жһқжңҲеҪұйҮҚйҮҚгҖӮж–°е»әзҡ„иҢ¶еұұпјҢдёҖжЈөжЈөиҢ¶ж ‘дёҖдёӘжҢЁзқҖдёҖдёӘпјҢжҺ’жҲҗдёҖжқЎжқЎз»ҝиүІзҡ„еҪ©еёҰгҖҒдёҖеұӮеұӮз»ҝиүІзҡ„жіўзә№пјҢжё©жҹ”жҒ¬йқҷгҖӮжҲ‘д№ҹиө°иҝҮиҢ¶й©¬еҸӨйҒ“пјҢдёҖжқЎжқЎиңҝиң’дәҺзҫӨеұұй—ҙзҡ„еҸӨйҒ“пјҢз”Ёе…үж»‘зҡ„йқ’зҹій“әзӯ‘пјҢзҹіеқ—гҖҒзҹіжқЎгҖҒзҹіжқҝпјҢзҷҫйҮҢгҖҒеҚғйҮҢгҖҒдёҮйҮҢпјҢзҹіи·ҜеғҸдёҖжқЎдёҚи§ҒйҰ–е°ҫзҡ„е·Ёиҹ’пјҢеҚ§дјҸдәҺиө·дјҸиҝһз»өзҡ„еҙҮеұұеі»еІӯдёӯгҖӮиҝҷжқЎи·Ҝжңүж—¶еғҸжӮ¬еңЁеҚҠз©әдёӯзҡ„ж ҲйҒ“пјҢжңүж—¶еғҸзӣҙйҖҡеӨ©дёҠзҡ„дә‘жўҜпјҢжңүж—¶еғҸз©ҝи¶ҠеіӯеЈҒзҡ„зҫҠиӮ е°ҸйҒ“гҖӮ
иҢ¶жҳҜеҺҶеҸІпјҢи·ҜжҳҜеҺҶеҸІпјҢеҺҶеҸІжҳҜдәәзұ»иҝӣжӯҘеҸ‘еұ•зҡ„и®°еҪ•гҖӮжҲ‘зҡ„з”ҹе‘ҪеңЁдёҖдёӘиү°йҷ©зҡ„з©әй—ҙпјҢеӢҮж•ўй—ҜеҶІиҝҮпјҢйқ зҡ„еҸҜиғҪе°ұжҳҜиҝҷжқЎеҺҶеҸІзҡ„и·ҜгҖӮ
пјҲдҪңиҖ…зі»дёӯеӣҪдҪңеҚҸеҗҚиӘүеүҜдё»еёӯпјү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