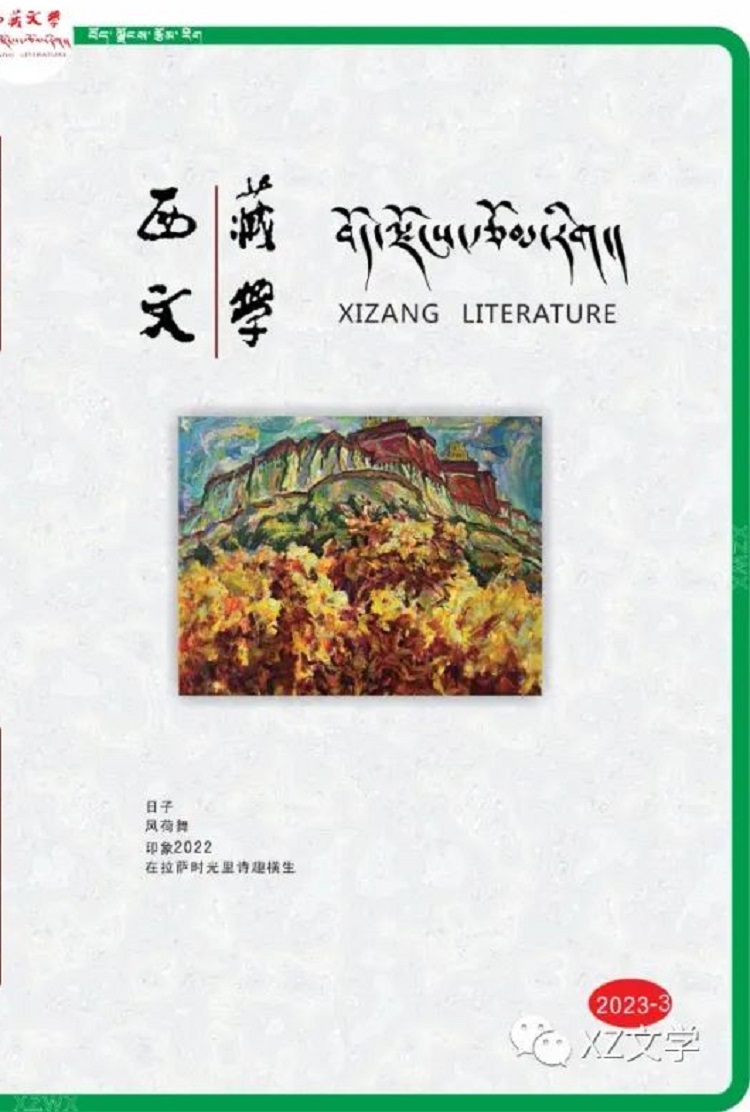
收到大姐的微信,正在基层调研的伦珠脑子一头雾水。同样的消息,让正在批改作业的丹珍愣了一下。
什么事这么打紧,非得见面说?
再过两天就是雪顿节,七天的假期省去了请假的繁琐手续。
放假第一天一大早,丹珍一家三口就出发了。
在高速上行使了二十多分钟后,车拐进了一条狭窄冷清的老公路,和高速公路并行一段后,老路委屈地拐进了更加狭长颠簸的乡村小路。路两边藏柳树和矮墙低调站立着,车子熟练地穿行其中。丹珍对这里太熟悉了。
绕过一座矮山头,眼前豁然开朗,青稞地和油菜花铺天盖地,宛如一幅画,村子就像镶嵌在青稞地里似的。乡间道路两边褐色的木棍栅栏,齐刷刷站成了迎宾队伍。
“小时候,这条路可宽了。”丹珍难言心中的喜悦。
“小时候的河水也都很宽。”强巴附和着爱人。
“我总是坐在这条路边等哥哥放学回来,”丹珍深情地回忆着,“同学给他的零食他都会带给我。”
“舅舅都给带些什么零食呀?”后座上的强珍好奇地问。
“奶渣,炒青稞粒,基本就这些。”强巴回道。
“舅舅他们也来吗?”强珍问。
没人说话。
车子经过了白色的村委会大院。
“比我们单位的办公室楼还要气派。”强巴带着羡慕的口吻。
“现在的村领导不仅观念新,脑子还灵。你看每年年底给大姐他们分的红,咱俩工资都是零头。”丹珍的脸上满是得意。
“那是,要不大姐哪来的50多万装修房子,‘土豪’在村里呀。”强巴望着窗外闪过的一栋栋二层楼房。这里已经打造成了县郊原生态休闲胜地,从春到秋,城里人蜂拥而至,爬山玩水,林卡放歌,美了人生。可枕着这么好的资源,这几年,丹珍兄妹几个却从来没有聚到一起。但这话强巴不能轻易提,说出去,那是在揭丹珍一家人的伤口。
远远地就见着大姐的房子了,强巴又一次问道:“你说大姐究竟有什么事呢?”这问题,伦珠夫妇也没琢磨出个究竟来。
“你说,你哥他们来吗?”强巴小心地问。
“我哪知道?!”丹珍绷着脸。
强巴下车,刚要敲红色的大铁门,门却开了。大姐和姐夫急匆匆走出来,只和强巴说了一句话。
强巴折回车里,刚下车的丹珍一愣。
“赶紧上车,我来开。”强巴不容分说把大包小包放回后备箱。
“怎么啦?这是怎么啦?”丹珍疑惑地上了车。
强巴发动车子:“准有事啊,大姐都顾不上告诉我。”
大姐车在前,强巴紧跟着,两辆车子飞驰出村子。
“不行,我得问问大姐。”丹珍不容分说拨打电话。
放下电话的丹珍,脸色凝重,呆若木鸡,半晌没吭声。
“没事吧?”强巴焦急地望过来。
丹珍不说话,却呜呜哭泣起来。
强巴不再追问,丹珍是个藏不住话的女人。
果然,没一会儿,丹珍就说话了:“哥哥他们出车祸了。”
强巴吸了一口冷气。
临出门时,伦珠见卓玛兴致不高,心里已经有几分不悦。
伦珠把带给大姐家的礼物装齐了,见卓玛不急不慢地收拾着儿子的衣服,他不耐烦地按响了汽车喇叭。
半晌,还是没动静。他气冲冲喊了一声,卓玛和儿子这才出了门。
一家人闷闷地不说话。儿子达杰是个闷葫芦,一上车就戴上耳机望着窗外,在自己的世界里享清福。
“哎,一会儿到了大姐家,别再蹦个脸。”伦珠面无表情地交代。
“我还是不去了,演戏演过头怕出岔子。”卓玛拎包准备下车。
“添什么乱?你心里怎么就没个数呢?”话一说出去,伦珠就立马后悔了。
“砰!”只听车门冷不丁关上了,卓玛已经下了车。
接下来的场景达杰太熟悉了。爸爸卑微地向妈妈道歉,脸上挂着死乞白赖的笑,妈妈翻着白眼不吭声,一副八辈子有仇的样。可要不了不一会儿,就像演一出戏似的,他们又该牵手折回到车里。达杰厌恶地闭上了眼睛。
音乐已经无法使达杰集中精力,妈妈骄横,爸爸软弱,他的冷漠无疑就是表达。
这会儿,爸爸和妈妈又有说有笑了。
“听你的,我们坐一会儿就回家。”伦珠笑着和卓玛说道。伦珠的笑里满是卑微,卓玛的笑融尽了得意。一声短促的“哼”从达杰的胸腔沉闷而出。
眼看着要上高速了,伦珠觉得什么地方震了一下,他还没反应过来,车子剧烈地就地旋转了一大圈,后面的车子已横在他面前。
穿过长长的过道,丹珍见着伦珠第一眼,竟忍不住泪流满面。如果今天哥哥发生什么意外,她是不可能原谅自己的。
卓玛一见丹珍,立刻转过脸去,闭上了眼睛。强珍冲到抢救室门前,紧张地往里张望。走在前面的大姐几乎扑向伦珠,伦珠语无伦次地告诉大姐,达杰在里面,情况不明。大姐顿时失声痛哭起来,她恨自己做出这样愚蠢的决定,如果达杰真有什么不测,她可是罪魁祸首,这家不是更加支离破碎吗?
丹珍和强巴尴尬地站着,低着头,像在等待审判。
之后的每天,丹珍都来医院,尽管哥哥和嫂子的脸色还是那么难看,尽管丈夫劝她不要再自找难受。是啊,那场车祸也不是自己安排的,可为什么总觉得自己愧对他们呢?
那天,丹珍又买了一锅鲫鱼,听办公室汉族同事讲,鲫鱼汤有利于伤口康复。走进病房时,恰巧嫂子的几位家人也在。碍于面子,大家聊了一句不痛不痒的话。丹珍把鱼汤交给哥哥,说鱼汤能促进伤口愈合。哥哥点了点头,但一直没有直视她。
她刚出门,就听见里面有人说道:“这汤可不敢喝,这样伤害生灵,治起病来哪能顺利呢?”“不是说喝这个伤口好的快吗?”“千百年来,我们的祖先不也靠喝牛骨头汤治好了骨折?有谁喝过鱼汤?”“我也听过鱼汤营养高,做都做了,浪费了多可惜。”“可惜,哼。你就不怕再遭报应?”“咦,什么叫再遭报应?怎么说话呢,走走走,都给我走!”
丹珍听见嫂子把那些人赶出了病房。他们吵闹着相互指责话说过了头,转而又把矛头指向了嫂子,说她不领情。
丹珍独自走着,街道人来人往,车辆东奔西跑,忙忙碌碌的,一刻都不停歇。她悲伤地想,人是多么脆弱呀,谁都无法预知不幸和幸运哪个先到来,今天出门的一些人有可能再也回不了家。侄子的命能保住,已经是万幸的了。可这话她不能和哥哥嫂子讲,她怎么可能希望他们能理解,换成是自己的强珍腿骨折了,她的心该有多痛呀。
强巴打电话问她在哪里,她一句话不说就哭出声来。
强巴是个聪明的男人,他极少评论丹珍兄妹家的那些事儿。他只是专心地听丹珍抱怨哥哥嫂子使脸色,嘲笑嫂子亲人的无情。大约一个小时后,她又在合计着明天该拿点啥去医院。
丹珍和伦珠兄妹俩,五官很像,同样的卷发,同样的褐色皮肤。但性格截然不同,丹珍心直口快,像一张透明的窗户,伦珠少言寡语,如一堵厚重的墙壁。望着丹珍的背影,强巴摇了摇头。
这几年,两家已经不来往了。但丝毫没有影响孩子们往来,强珍和达杰常常约着一起玩。强珍看不惯妈妈和舅舅老死不相往来的样,悄悄话她都是讲给爸爸听。强巴当然死守着与女儿的约定,从来不把孩子们的事情透露给丹珍一丝一毫。
达杰生在春天,强珍生在夏末,强珍管达杰叫哥哥。达杰和家人话不多,和强珍在一起,仿佛换了个人。强珍笑起来像太阳,他喜欢这个妹妹的开朗、善良。
两家关系僵持着,他更加珍惜这个妹妹。他们都喜欢吉他,小时候周末去吉他班,都是两家争着送。小学一年级起,兄妹俩上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级,从未红过脸。整整六年,两家轮流接送孩子,一团和气,令很多人羡慕不已。
这本该是延续的温暖亲情,没承想却意外断了线。每当母女俩发生争吵,强珍会理直气壮地把这解不了疙瘩的账,一股脑算到丹珍那次愚蠢的决定。丹珍也后悔,但如果哥哥嫂子心胸不那么狭窄,何至于此。
三年前的六月,强珍和达杰小考。到内地读西藏班,意味着更好的教育条件,更好的出路,当然也包含父母脸上的光彩。从四月份开始,两家铆足了劲,做足了功课。他们千方百计改善孩子们的饮食,四处打听请到最好的家教辅导,起早贪黑陪孩子背书,不厌其烦帮孩子查阅各类考试资料。
考试当天,丹珍和卓玛换上了新定做的藏装,头发都是到理发店专门做的,两人既紧张又激动,泪花都在眼里打转。她们如敬业的模特般,始终保持着饱满的激情在考场外站到第三天考试结束。兄妹俩胸有成竹,神采奕奕出考场的状态,让两家爸妈悬着的心总算安稳了些。在等待的日子里,两家暗自准备着新的行李箱和孩子要用的银行卡、手机卡、藏装等用品。
一天夜里,丹珍打来电话说成绩可以查了。伦珠夫妇朝儿子卧室狂奔,可儿子却把门关得死死的,任他们说破嘴皮都不吭声。他们赶紧喊强珍来,强珍进去坐了很久很久,出来只说了一句话:“舅舅舅妈,哥哥心情很不好,你们给他点时间。”
卓玛瘫坐着,大脑一片混沌。伦珠来回踱步,如同困兽。
丹珍想要说服哥嫂,让达杰跟着他们住几天,伦珠坚决摇头。
这几天,丹珍天天打电话询问达杰情况,打来的电话多了,卓玛的语气开始变得越来越生硬。
“她是巴不得我们达杰出点事,天天问,明摆着没安好心。”卓玛撂下电话就喊,一次比一次愤怒。说多了,就连伦珠也觉得这妹妹有点看热闹的劲头。很多次,显示是丹珍家号码的,他俩谁都不理睬。现在,除了儿子,其他的都无关紧要了。
强珍几乎隔几天就去看哥哥,每次都是半天,但她对聊天的内容守口如瓶。每次问达杰的情况,强珍都会用“别瞎掺和,这些事情需要哥哥自己来消化。”来堵丹珍的嘴。
强珍考上了上海的西藏班。这几天单位里都是小考的话题,强珍的高分赢得了同事们赞叹。夫妻俩神清气爽地上了几天班后,按照之前的计划,申请年假,要亲自送强珍去上海的学校。
强巴的亲戚和丹珍的闺蜜们都在鼓动他们为强珍举行欢送会。两人思前想后,还是动了心。这些年,两人送去的份子钱也足够多,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,也算是收回成本吧。
“你和大姐、哥嫂他们也打声招呼吧。”决定要办欢送会后,强巴提醒道。
“哥嫂都不问强珍考试成绩和学校情况,他们也太过分了。”丹珍这话其实说到了强巴心里,但他没吭声。
“嫂子那么要强,我怎么觉得这事有点难开口。”丹珍露出少有的无奈。
“周末,我们约哥哥一家去吃个便饭,合适的时候你说一嘴就好。”强巴建议。
饭局没约成,哥哥一家出了远门,这是强珍无意提起的。
“他们可真有意思,出门还带保密的。”丹珍气不过。
“舅舅舅妈带着哥哥散散心,多好的事情。”强珍没发觉妈妈的不悦,“只是可惜哥哥不能参加我的欢送会。”
“可惜什么,瞪大眼睛瞧瞧谁才值得你可惜啊。”丹珍用手指狠狠地点了点女儿的脑袋。
临睡前,丹珍又说起这件事情。她放不下,强巴心里也多少有点火。达杰没考好跟自家不相干不说,连句场面上的话都不闻不问的,越想越不像话。
后来的三年里,两家也没有什么名正言顺的理由,越走越远,就连回大姐家也都是你走我来,从不碰面。久而久之,倒显得相互碰面是件极其尴尬的事了。
“她大张旗鼓地举行欢送,是显摆给我们家的。她要低调点,达杰能不吃不喝的,弄情绪?”伦珠和卓玛振振有词。
“是个不太相干的人都会问学校情况,毕竟孩子第一次离开家去那么远,欢送时他们不表示就算了,假装关心一下也很难吗?还亲哥哥呢!”丹珍说着委屈地落泪。
大姐无奈着急,可任谁她都说不过。伦珠和丹珍都是有文化的人,她一个乡下人,怕是理不清、断不了这案。
瞧见医院走廊里伦珠失魂落魄的样子,卓玛对丹珍恶狠狠的眼神,还有紧闭着的抢救室大门,大姐的心里流出了血。阿妈过世后,她就成了家里的当家人。每每想到亲弟弟妹妹跟仇人似的相处,她焦灼万分,甚是自责。想来想去,她和老实巴交的老公商量了办法:编个理由,让俩人都同时回家,用尽浑身解数,当面解开这个疙瘩。可这办法多蠢啊,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。她恨老公的馊主意,更恨死了自己的幼稚。现在,她唯一的希望是达杰能够平平安安的。只要孩子能健康地活着,她以后再也不瞎操心了。弟弟妹妹在城里各自成家,各自有事业,各自平安就好,一家人也不一定非要围坐一起了。想到这里,她的泪水再一次控制不住地流下来。
抢救室门开了,医生走出来,面无表情地说了句:“病人脱离危险了。”过道里,没有拥抱,各自哭泣着。
达杰的膝盖做了手术,强珍天天陪在病床前,给他听音乐,陪他聊游戏,喂他吃好饭。
伦珠和卓玛艰难地从崩溃的边缘爬出来,身心疲惫,日渐消瘦。他们在抢救室门口像纸片一样脆弱的样子,刻在了丹珍脑海中。在生与死面前,除了平安一切无需牵挂,也无意义。
大姐用自己的方式四处拜佛,请求佛祖宽恕自己的罪过,请求药神保佑达杰。丹珍不厌其烦,一趟一趟地送饭。卓玛尴尬地接过,伦珠每回都不做声,只有达杰和小姑说话。
强珍去江苏读高中,达杰回家又休了一年学。他每天都在翻阅着强珍送来的日本动漫资料,只有这个妹妹知道自己真正爱什么。两人还商量了要练习的吉他曲目,约定找个时间一起表演。
达杰整天躺在床上,除了漫画书没见他翻看课本。卓玛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,他这明摆着是糟蹋自己,本来初中就晚了一年,现在又碰上这倒霉的车祸,离高中的门槛整整晚了两年。卓玛暗自落泪,她哭命运不公。她既恨儿子不争气,又心疼儿子伤腿。丹珍一家人常挂在嘴上的诸如“早一年两年毕业没啥差别”“孩子健康最要紧”“很多成功人士上的都不是名牌学校”此类的安慰,让她倍加反感,异常恼怒。他们是来看自己家笑话的,内心有声音告诉她,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真切。她谴责自己的一再迁就,憎恶伦珠的忍气吞声。她痛定思痛,几次想要开口,可转而又难以启齿。达杰恢复得这么快,性格也开朗不少,不能不承认强珍的鼓励是起到了大作用的。
卓玛45岁从单位退了下来,全心照顾着达杰。可没承想,退休后的处境令她几乎窒息。
“我说我不喜欢读书,我要学漫画。”达杰歇斯底里地喊叫着。卓玛说不出一句话,只是狠狠扇了达杰一巴掌。两人都惊愕地望着对方,达杰不相信是妈妈的巴掌打在了自己脸上,卓玛更不相信自己会抡起手扇儿子。
等伦珠赶回家,卓玛双眼红肿,颓然发愣。达杰头蒙被子,纹丝不动。床上、地上到处仍满了课本,茶几上的碗东倒西歪,酥油茶油渍白花花的,从桌上到地上满是的。
伦珠刚得知自己在单位民主推荐会上失利,窝着一肚子的火。听卓玛絮絮叨叨说了半天,他怒了:“你小子别犯浑啊,你要不上学,那就滚出这个家。”
卓玛吃了一惊,原以为搬个救兵能救火,不想那是火上浇油哇。她噌地起来,拽着伦珠往卧室走去。
“怎么说话呢?”卓玛把门关牢,瞪大了眼,指着伦珠的鼻子。
“去,你会说别叫我啊!”怒气之下,伦珠黝黑的脸露出凶恶。
“你就会在家横,有本事对着你那些幸灾乐祸的亲人吼去。”卓玛尖叫着,拳头在伦珠头上、胳膊上乱捶。
“泼妇一个。”伦珠甩开卓玛扬长而去。长久,达杰还听见妈妈在卧室里哭泣。
孩子的事情终究是大事,当天晚上伦珠又是道歉又是承诺又是发誓。和好后的两人开始苦口婆心,讲道理,摆事实,回忆过去,展望未来,可达杰却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坚定。
卓玛彻底失望了,眼看着亲朋好友的孩子一个个要上大学,而达杰……她不敢想象靠着画画能过上什么好日子,她仿佛看见达杰不修边幅,满身水彩印,孤独地坐在一张画架前,满地的白纸似乎透着无奈和落魄。到那一天,她该怎么面对?她又想到了伦珠,本是单位学历最高的人才,但时运不济,每到提拔时,一波波年轻的空降兵悄然而至,伦珠的副处级眼看着也将化为水泡。如今岁数大了,带出的徒弟都当上了他的半个领导,他应该也恨不得早点结束这尴尬难堪的日子,可又能指望谁呢?自己在单位本就一极不起眼的工人,又是退休职工,达杰不上大学,在高学历毕业生成堆的时代这不是诚心让人笑话吗?她前思后想,激愤满怀,忧虑不已,夜不能寐。
连续三个月夫妻俩不停地开导达杰,一会儿和颜悦色一会儿怒目相视,尽管他俩每天口干舌燥,精疲力竭,达杰依然无动于衷。卓玛请来了达杰的几个好朋友,提前和他们千叮咛万嘱咐,可孩子毕竟是孩子,没一会儿功夫,竟聊起了NBA!无奈之下,伦珠托人请到了教育部门的一位老师,恳请老师救救他的孩子。老师高个子,白皙脸庞,一身休闲装,谈了没多久就从达杰卧室走了出来。伦珠夫妇急于从他脸上看出点什么,可他却招呼他们坐下。
“这孩子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,他已经下定决心了。作为父母,更需要冷静。”老师谈了很多很多,伦珠只记得这句话。
“他这是浓疮长在别人身上不心疼,一通胡说八道。”卓玛几乎要崩溃了,对着老师的背影骂骂咧咧。
一天天,日子像长了翅膀似的,好像邻居的小宝宝昨天还在推车里吸着奶嘴,今天就看见她背着书包上了学,让人慌了神。卓玛想尽办法,又是哭又是闹,又是几天不回家,达杰依然纹丝不动,守着他的画板。那些画板像把剑,戳进了卓玛的内心,绝望的她伤痕累累。可她依然在努力,因为她是妈妈,一步错步步错,可不能因为达杰一时糊涂毁了好前程。
她把自家能说上话的人都请来了,一个个和达杰谈,可任谁苦口婆心,达杰毫无退缩之意。卓玛几乎要疯了,家里经常听见锅碗瓢盆叮当摔打的声音。她整夜整夜的失眠,在失眠的漫漫长夜里,应证了那句老话“人比人气死人”。强巴参加工作比伦珠晚几年,人家早就副处了。可伦珠又一次失去了晋升机会,往后更是没指望了。卓玛的气更不打一处来,她心里憋屈的那叫苦哇,恨呐,她冲伦珠发泄着:“你自己窝囊不说,也不好好教育孩子,诚心给人看笑话。”伦珠也不反驳。
时间长了,伦珠和达杰都学乖了,任卓玛发脾气,诉大苦,两人不声不响。卓玛除了偶尔和两个发小去茶馆外,大多数时间都在家里为达杰和伦珠准备三餐,里里外外打扫卫生。她几乎不怎么歇息,也不看电视,也不怎么玩手机。达杰看在眼里,也心疼妈妈。妈妈还年轻,可她消瘦,头发稀疏,皱纹清晰。妈妈为了他操碎了心,可达杰知道,妈妈必须得接受,只是早晚的事。
果然,一年多过去了,卓玛似乎再也吵不动了。达杰在八廓街一家唐卡画室当学徒,他每天都沉浸在多彩而庄重的世界里,充实而激动。伦珠去过几次画室,师傅说达杰的心很静,说他既有天赋又勤奋,只要能够坚持,他会是个好的唐卡画师。
伦珠把师傅的话讲给卓玛听,卓玛装没听见。
达杰从画室回来,除了吃饭,几乎都在卧室里画画。有一回,卓玛不经意间打开了达杰的房门,眼前的情景让她大吃一惊。墙上,桌子上,床全是画,画板下方莲花盛开着,纯洁无暇,卓玛上前轻轻摸了摸画,又赶忙缩回手。自从达杰选择了和她唱反调,她就发誓不再给他打扫卧室。可现在,当她环视小小的卧室,除了被子,满眼都是画,张张画的那么用心。她不由地呆住了,想到自己这一年多的努力和失落,她的泪水不自觉流下来。如今,她累了,没有选择了。这就是达杰的生活,他将和这些画融为一体。这也是她的生活,别无选择。
之后的每天,达杰都会发现卧室被整理过。再后来,家里把储藏室腾出来,达杰就有了自己的学画室。
很多时候,伦珠会陪着达杰在画室里呆上很久。唐卡画室的生意越来越好,师傅对达杰寄予众望。伦珠又开始唯唯诺诺地讨好卓玛,时不时地在卓玛面前夸赞达杰的画功和勤奋。卓玛的笑容如早春柳树吐出的叶芽,因为稀有,使人惊喜。
日子仿佛就要这样如春风般软软,轻轻地划过,卓玛一家人兜了一大圈,又和气地坐在一起。谁也不提那些闹心的往事,关起门来,他们都很知足。
可人毕竟不在孤岛生存,谁也经不住欲望拍岸卷来。风波发生在盛夏。按照达杰发来位置,卓玛和伦珠到达拉萨河对岸的一处藏式庄园,庄园院子里各色海棠花怒放,过道里摆放着很多传统藏式家庭用具,有些就连卓玛都没见过。在一位美丽服务员的带领下,他俩来到了二楼叫“扎西康桑”的包间。包间很大,除了中间的大圆桌外,其他摆设与藏族家庭客厅无异,家具和墙上的装饰很是讲究。透过宽大的窗子,可以远望布达拉宫,在阳光照射下,金碧辉煌,壮观威严。强珍穿着藏装迎过来,达杰坐在椅子上,微微笑着。
“你们这是?”卓玛吃惊地望着达杰。
“我们俩的吉他演奏会。”没等达杰反映,强珍激动地说。
“好像达杰没长嘴似的。”卓玛轻声嘟囔着。
伦珠猛地拽她坐下,大声说:“太棒了,我得好好欣赏欣赏。”
卓玛扫视了一眼,心里正犯嘀咕,就听见门打开。大姐姐夫带着俩孩子进来,见卓玛和伦珠也在,大姐先是一惊,随即加快脚步高兴地走上前。强珍拉着其他人就坐,服务员为大人们倒上了甜茶,给年轻人摆上了冰镇饮料。
“今天可真是好日子。”大姐难掩心中喜悦,目光来回扫过每个人的脸,不知疲倦。
卓玛看了看桌上的人,也露出难得的微笑。她起身给大姐添了茶,不卑不亢地问候大姐一家。大姐夫正和伦珠聊着房屋翻新的话题,孩子们嘻嘻哈哈异常热闹。
大姐朝自家老公望过去,眼神里满是疑问和焦虑。他太懂她的心思了,冲她轻轻地摇了摇头。这一切没能躲过卓玛的眼睛,其实她心里也在嘀咕。听见强珍对服务员说,可以上菜了,卓玛松了一口气。
庄园的藏餐很地道,碗盘古香古色,大姐尤其喜欢藏式茶壶,服务员见客人喜欢,特意用传统习俗轻轻晃动几下,再慢慢添茶,大姐惬意地点着头,直夸强珍和达杰会选地方。
大家兴致勃勃地聊着包间的精美装饰,以及庄园老板选择位置的独到眼光,气氛热烈。
“不好意思,来晚了。”门突然打开,丹珍和强巴被服务员领了进来。
“就知道你们不守时,我们已经开吃了。”强珍马上把爸爸妈妈安排在姨姨左侧。
大姐的眼里闪着泪花,她的目光从左侧的丹珍夫妇扫向右侧的卓玛夫妇。她欲言又止,向强珍举着大拇指表达着此时的激动。
卓玛的脸刷地变了,她冷冷地低头喝着茶,眼皮都不抬一下。大家都注意到了这个细节,伦珠假装接电话,出了门。
“一会儿,我和哥哥有个小演出,请大家多多指教。”强珍大声说着,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她和达杰身上。
“哥哥,你说。”强珍转向达杰,达杰还是那张腼腆的笑,但今天他答应过妹妹,一定好好配合。他清了清嗓子说:“我们的演出免费,希望所有家人都喜欢。”
大家又是鼓掌,又是叫好。一阵热闹后,谁都没说话,只有筷子触碰磁盘的声音。
“演出什么时候开始啊?”伦珠进门打破了尴尬的局面。
“就现在吧。”达杰说着,示意强珍站起来,两把吉他早已准备停当。
气氛又一次热烈起来,人人都兴奋地等待着。达杰坐在椅子上,强珍在边上站着,两人的手灵敏地在琴弦上舞动,优美舒缓的节奏响起,一首《夜色中的布达拉宫》缓缓弹出。达杰用轻柔的声音唱起了歌,强珍投入地配合着。大家屏住呼吸,他们难以置信,达杰居然唱起了歌,而且是如此的动听。一曲唱罢,掌声不断。大姐泪流满面地站起来,走上前用双手激动地捧起达杰的脸,用额头深情地碰了碰达杰的额头,大姐的白发挡住了达杰一头黑发,卓玛的视野也已被泪水彻底遮住,她控制不住地抽泣起来。
“姨姨,这才开始呢。”强珍总是很机灵。
第二首歌是《南飞的大雁》,第一段是强珍用藏语唱,第二段换成了达杰用汉语唱。这柔美的歌声软化了大家紧张的内心,他们嘴里轻声和着,双手打着拍子,完全陶醉其中。
第二首曲唱完,丹珍给俩孩子献上了哈达,气氛更加热烈。
“咦,怎么只有你有哈达?”大姐叫着。
“我刚才让服务员去买的,这就代表大家了。”丹珍笑着解释。
“哼,说的自己就跟当家的似的。”卓玛板着脸轻声嘟囔着。
卓玛的话大姐听得一清二楚,打进入这个包间,大姐的心就吊着,她小心翼翼的说话,甚至都不敢提议大家一起敬俩孩子。
“我们就好好听歌,孩子们的歌多好听啊!”大姐慈祥而求助地望着强珍和达杰。
“对对,妈妈你就别添乱了,后面还有哥哥自弹自唱呢。”强珍用调皮而又撒娇的语气激起了大家兴致,大家再次鼓起掌来。
看得出,对于今天要弹的吉他曲,两人是精心挑选了一番。当第三首歌曲弹起时,大家一下子安静下来。这首《我们再此欢聚》是藏族人欢聚场合必不可少的歌,寓意欢聚的愉悦和彼此真诚的祝福。
大家跟着节奏一起唱起来,大姐深情地望着大大小小十个人,本该就是这样亲密无间,骨肉相爱啊!她不停抹着泪,她太感激这俩孩子了。想到伴着今天的歌儿可以让家人见冰释前嫌,她是多么的欣慰啊。
接下来,大家听到了达杰独唱《慈祥的母亲》。这首饱含儿女对母亲浓浓爱意的歌曲,在每个人心间注入了更强烈的暖流,达杰深情演绎,听得个个如痴如醉。卓玛不停用纸巾擦拭着泪水,伦珠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背。丹珍紧紧地挽着大姐,眼里露出柔和的光。这些年,她和哥哥各自成家立业,在急促的行走中,各自捍卫着自家的尊严,一家人越走越远。面对着她和哥哥的任性,伤心而柔弱的大姐无能为力。丹珍太懂大姐了,今天这一幕是大姐日日盼月月盼的情景。望着大姐止不住的泪花,丹珍心怀愧疚。
“我建议我们一起举杯庆祝一下,是不是,姨姨?”强珍兴奋的满脸涨红,她和哥哥的辛苦总算没白费。
“那是那是,来,祝我们全家吉祥安康,扎西德勒!”正在兴头上的人们举起茶杯、酒杯、饮料,跟着欢呼扎西德勒。
“你俩去和你哥哥嫂子碰一下杯。”大姐轻声提醒丹珍。可丹珍却笑了笑没动。她不是迈不开腿,她是开不了那个口。强巴见丹珍没动,也装作没听见。
“达杰,你太厉害了!即使你不去画画,完全可以唱歌养活自己。”丹珍真心夸赞达杰。
“什么叫靠唱歌养活自己?现在达杰就不能养活自己了?我就看不惯你高高在上的样子。”卓玛蹭地站起来,大声叫嚷着。
“嫂子,我真不是这个意思,我真是替达杰高兴。“丹真诚恳地解释。
“我不是你嫂子,你也别把自己说那么高尚。”卓玛涨红了脸。
“人家不是这个意思。”伦珠在一旁拉卓玛坐下。
“别拉我,什么都是人家好,人家对,就你窝囊。”卓玛一把甩开伦珠的手。
“我哥窝囊,也是你弄得。”丹珍毫不示弱。
“呦!一家人合起伙来欺负我,我不吃这一套。”卓玛突然起身,破门而去。伦珠白了一眼丹珍,也跟着出了门。
这突然的变数,让强珍和达杰措手不及,他们愣愣地望着,手中紧紧握着吉他。他们想不明白,大人们这一切到底又是为了什么?
“你呀,就不能看在孩子们的面上忍忍?”大姐伤心地责怪着丹珍。
“凭什么啊,您没听见她说话多难听。”丹珍毫不掩饰内心的愤怒。
“妈妈,你太让人失望了,简直不可理喻。”强珍带着哭腔。
“你少来,要不是今天你瞎闹,我至于这样嘛。”丹珍怒视着强珍。
“你,你,你就是太自私。我宁可没有你这样的妈妈!”
强珍哭叫着。
“我们只是想让亲人不再那么陌生。”伦珠低声说道。
“你少说几句话,别再伤着孩子们的心。”强巴劝丹珍。
“想让我少说话,那我就走,省的你们闹心。”丹珍狠狠地摔门离去。强巴迟疑了一会儿,对大姐说了话道歉的话,也跟着出了门。
包间里,一阵沉默。
突然,碗碟碎地的声音使大家惊醒过来。只见大姐露出痛苦的表情,用手握住胸口,趴在了桌子上。剩下了六个人乱成一团,哭叫声,喊叫声,跑动声,直到急救车到来。
“你们这些人,会要了她的命。”大姐夫愤愤地自言自语。
急救车载着大姐一家远去。
强珍和达杰呆呆地望着满桌的冷盆冷菜,散落一地的碗筷酒杯,狼藉如此时他们的心情。
原刊于《西藏文学》2023年第3期

达娃央金,女,藏族,西藏作家协会会员,发表有大量散文、小说,出版短篇小说集《敲开那扇门》,曾获第八届“西藏新世纪文学奖”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